夜读|我那不懂父亲节的老父亲
父亲节前夕,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和上幼儿园大班的儿子忙着给我准备礼物,神神秘秘的,不想让我提前知道。无论是一张写有暖心寄语的卡片,还是他们眼中的“我的素描”,抑或是一张全家福照片的装饰品,他们都学会了大方地向我表达感激之情。
这种情绪表达对于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很常见。但是对于从小生长在农村的我来说,我是很陌生的。性格内向,沉默寡言,尤其不善于直接向家人表达感情,是很多农村孩子的通病。
我从未直接表达过对父亲的敬仰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: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父亲。
我父亲出生于1949年。他当了地主后,小学二年级还没读完就被迫辍学了。从此告别了学生身份,开始了农民的终身身份。那一年,他八岁。
爷爷在外地工作,常年在外。一大家子的生计全靠奶奶。在田间地头,在家门外,身高不足1.5米的奶奶永远无法休息。父亲作为长子,自然是最重要的帮手。他小的时候,经常把我二叔背在背上,把我三叔抱在怀里,手里拿着镰刀割草或者放牛。
短短几年,他学会了农活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两项技能——翻耕和犁地,已经是一家之主。那一年,他十二岁。
从此,从播种、插秧、割粮、碾米等农事,到请客送礼、置办年货、举行祭祖仪式,家里家外的一切都由父亲负责。
父亲是村里公认的“能人”。他从来没有当过老师,但他愿意努力学习,成为一名自学成才的人。他非常精通盖房子、煮饭、挑屋顶和修理电器。村民遇到处理不了的事情,总会先想到他。
父亲没文化,但绝不允许孩子没文化。90年代初,父亲去了省会武汉的一家砖厂,独自打工,干着脏活,挣着微薄的工资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一砖一瓦翻过来,一砖一瓦翻过去,不知多少砖瓦日夜操劳,为我和弟弟读书铺路。
我在武汉大学的四年,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父亲那里进行牙祭。砖厂食堂的饭菜很差,菜里没什么油。父亲总是用电饭锅给我做排骨玉米汤。记得有一次,下午一点多,我去他那里。爸爸下班前,我先吃饭。太油腻了。勉强吃了半碗,听了听广播,自然入睡。
醒来的时候,我看到爸爸在吃我剩下的半碗。我心里难受,暗暗嘲笑他的迂腐。
直到我来广州读博,父亲才辞掉工作,回到农民的身份。
如今,父亲已经73岁了,每天还在工作。我和我哥一直叫他少种地,他不听。
每次我给他打电话,他几乎都在忙:割稻子或者拔花生;不是帮人造炉子,是捡瓦片;要么在河里铲沙子,要么在镇上盖房子。他的原话是,“不能闲着,久了就没精神了,动起来更舒服。”
今天早上,我打电话给我父亲。说起父亲节,他一点反应都没有,只是在抓他的鱼。在父亲的地方,只有工作和忙碌,没有节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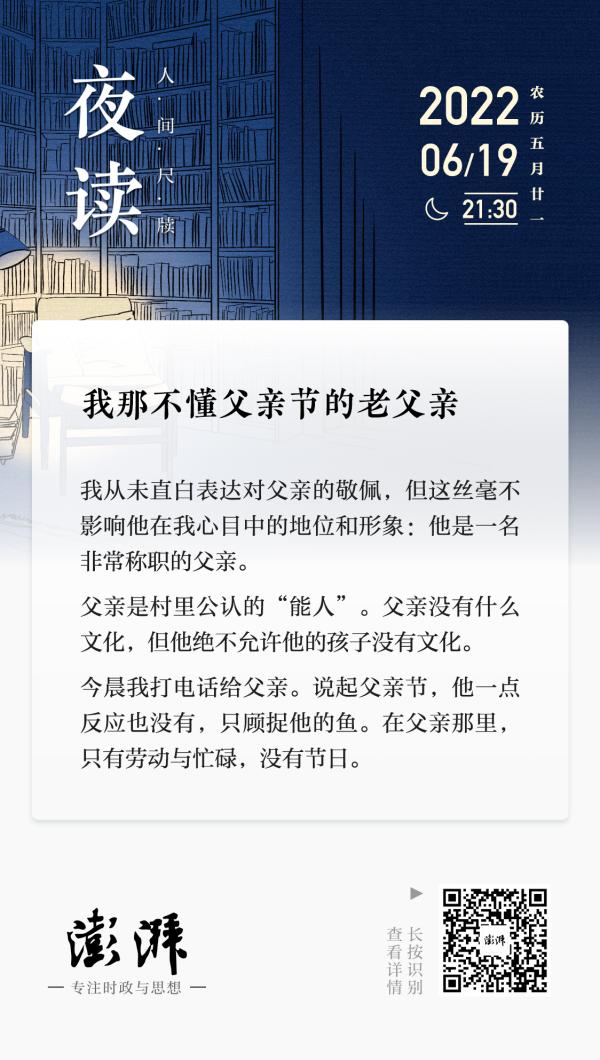
(本文来自论文。更多原创信息,请下载“The Paper”APP)
作者:姚华松
- 发表于 2022-06-22 09:20:59
- 阅读 ( 349 )
- 分类:科技